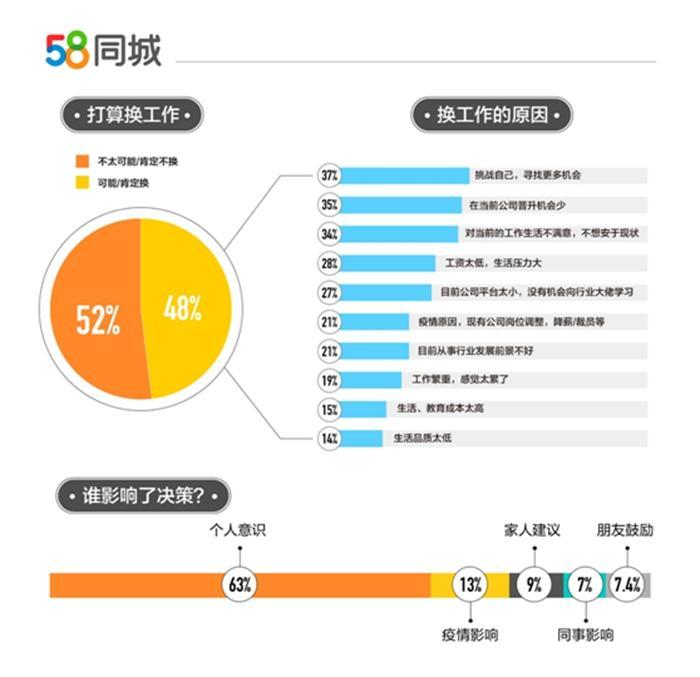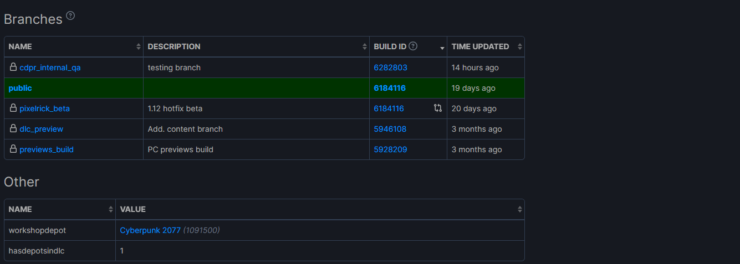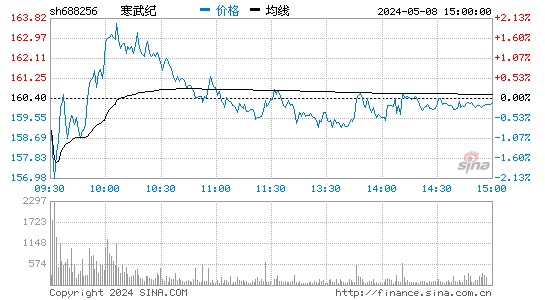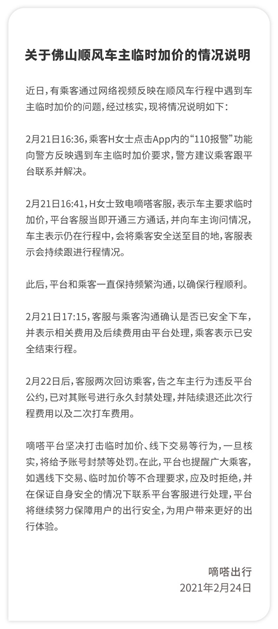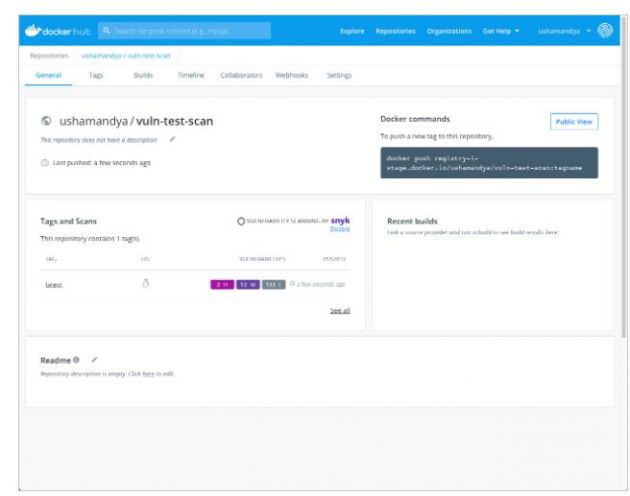原标题:文穴书评|《纸上行舟》逃逸与翻转


《纸上行舟》
丛书:后浪·说部
出版社: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
作者:黎幺
图书简介
在本书所收录的八篇短篇小说中,作者展示了如何以架构一个个离奇异境的形式来重新定义日常事物。书籍、榨汁机乃至抽象的概念也能如生命形体般活动吗?一个人怎样如一条蜕皮的蛇般从他的身份中出离并最终散去无踪?在灵台方寸山上学习七十二变的猴孙与当代上班族有何联系?世界末日之后,一台写作机器竟然以「逆向符号化」的方式吞并了现实?
超现实的异境、绵密饱满的语言、精细锻造的文体,这些因素使得作品诗意旋转,由此产生独特的阅读快感。
正文
约定俗成的秩序将事物框定成寻常图景后,我们的世界亦变得「平铺直叙」。它似乎更容易把握,但在少了许多「危险」的同时,也不再细腻富饶、趣味盎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世界仿佛理性的牢笼,合理分类的网罗。它将我们的生命囚禁,令我们屈从于所谓的现实。
当一种分类秩序使用得太长久太普遍,在它的宰制之下,世界的光泽亦被遮蔽,事物的肌理被磨损,褶皱被碾平。
然而,这绝非世界的唯一真相和面貌。
因为在平铺直叙的世界底下,是永恒无尽的冲突,是欲望时刻在低语、奔涌和咆哮,它有着无数迷宫环绕、峰回路转与柳暗花明。
艺术家是逃逸者,始终在偏离「平铺直叙的世界」。艺术家殚精竭虑地逃离庸常秩序的捆绑,他们渴望发掘平铺直叙之外的另一面,从而将人从陈词滥调的包围中拯救出来,以新的眼光打量和打磨世界。作家黎幺凭着天赋与勤奋,成为一位语言艺术家,他像炼金术师般引领我们在日常之物中穿梭与冒险。
倘若一定要将黎幺的《纸上行舟》命名为小说,它也与通常意义上的小说迥异。因为他笔下那些或长或短的篇什往往缺乏使大多数小说得以成立的故事情节,即便你读后也难以复述,更多是一堆复杂感受。但故事的缺席并未使黎幺的小说贫瘠,它们反而在挣脱完整情节的束缚后收获另一种天马行空的丰饶。那是对既往法则与逻辑的损毁、压缩与重造,它们无需顾虑一个故事是否完满自洽,而是让话语凭着想象力游弋、冲刺,文本亦成为言语的狂欢与合奏。
《纸上行舟》容易引发错觉,使我们以为在黎幺的妙笔之下,任何事物都能成为他另类小说的主人翁(尽管这是充满悖论且引人误解的说法)。
以《机械动物志》为例,无论是微不足道又遭人厌烦的蚊子,还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半头大象,它们都堂而皇之地成了黎幺刻画的主角。更令人震惊的是,榨汁机,一座城市,甚至「茫然」与「晕眩」等人类状态,也得到他热烈的邀请,变成那些叙事片段里的核心角色,拥有了出人意表的生命力。
但我们亦无需大惊小怪,因为黎幺的笔总是使不可能之事成为可能。当我们得知黎幺有一篇小说的主角是一本叫做《平行与交叉之圆》的小说,我们不应过分诧异,而应会心一笑。没错,一本小说成了这篇小说的主角。(我们立即联想起博尔赫斯,他正是通过给一本本在想象中存在的书写序而完成了小说创作)
黎幺是隐匿的博学者,他一定暗自贪婪地或咀嚼或吞噬着各种各样的书。不论是文学,还是哲学作品,都会激起他的热情。他未必将晦涩的哲学理论再次体系化,而是摘取、揉碎,让它们的吉光片羽融入自身的感受与想象。思想与悖论如影随形地伴他的文本前行,而我们对他的阅读也成了一次次回味与操练。
黎幺笔下时常涌现一大段一大段格言,一再证明他对思想的爱好:
「……隐含着一个悖论:最有效的传播是对传播的拒绝。或许也可以总结为,将某个消息定义为秘密,是将之昭告天下的最佳手段。」
「他们活在一首诗里,只有他们自己读不到。」
「时间的流逝像表演」。
这位拥有格言家才华的小说家却全无说教口吻,他只是将这些精彩的警句点缀、装配进文本的缝隙中。一个意象在黎幺书中反复出现——自我吞噬与自我繁殖。
「接下来请想象一条咬尾蛇,一根穿过自己针眼的针,尤其是一个在子宫里孕育自我的女人。」
「他从一只桃子中剥夺桃子,从一枚桃核中剥夺桃核,再从一粒桃仁中剥夺桃仁,直至得出一个完全干净的1。」
「这种吞食让他重新出生,重新成为自己的母亲。」
「他们骑乘着自己,荒谬而不由自主地鞭打自己。他们是一群蜂拥而至的疏离感,他们追赶着,但除了自己的影子,仿佛什么也没有追赶。」
「像果肉包裹着果核。」
「我的故事在以书写来呈现书写的荒谬中,被绕进了一团乱麻般的自反馈系统。」
这些意象的诞生当然与黎幺对悖论的沉思密切相关,又与他醉心阅读无法分离,它们都是关于阅读的隐喻之变体。阅读不总是在自我吞噬又自我繁殖吗?语言在不断地裂变与再生中,将我们带向时间的黑洞里。
对阅读与书写或隐或显的执迷与讴歌,布满书中所有角落,不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带着阅读制造的想象」,抽取自《纸上行舟》某一页,这个如今因被我腰斩而残缺的句子,恰恰最适合形容黎幺本人的写作。
他某些小说的起点一定与阅读有关。曾经阅读过的书如幽灵般对他纠缠不休,他一转手就将它们变成自己「空中楼阁」的秘密地基。有些篇章的源头显而易见,如《柒拾贰》与《猴的越狱:一则镜子的寓言》。它们的灵感取自《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黎幺笔下的孙悟空,在《柒拾贰》里甚至被剥夺了名字,只成了「孙」,他不再无所不能,而是在历经想象的变幻莫测后,突然变成上海这座巨无霸城市里茫茫人海中最普通的一个上班族,这是七十二变的最后一变,这一变的结局因为最平常而显得最魔幻。故事的结尾是他醒了,出门去买可乐喝。在想象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里,黎幺把主人翁在从梦中拉回琐碎的现实世界,就此也完成了他对过去文本的彻底翻转与重新编织:《西游记》中残存的七十二变有多奇幻,黎幺小说主人翁的现实处境就有多平庸。
《猴的越狱:一则镜子的寓言》中的石猴还可怜地拥有孙悟空的某些特性,但他的反抗最终沦落为对镜子的反叛,戏谑而又悲凉。这或许是黎幺最深处的忧郁间歇性「发作」:
「猴子们获得的只是表面上的自由,那面不存在的镜子依然奴役着他们。……对称法则仍然有效:在这一边灵魂堕落,在那一边肉体腐朽。」
如此意味深长的结局,不过是对人类处境的揭示。
《机械动物志》里的两个短篇也关乎阅读的隐喻。《一种为解读而生的动物》写斑马,其实只是对白纸黑字的书本进行奇特想象,黎幺以斑马的繁殖与被捕猎比拟文本的生产、阅读。黎幺用《蚁穴逃生》来譬喻阅读,阅读就像进入蚁穴,文字就像蚂蚁一样爬满洞穴,读者只有不断穿过蚁群,才能找到秩序与出路。这个比喻十分形象地描绘了我们面对无数文字压迫时的窘境。
通览《纸上行舟》全书,我们看到它有现代主义文学印痕之外,也能窥见中国笔记小说在文本的变异。黎幺融合此两者,并加以改造。他在序言中写道:
「我并不认为写作是一种「出窍」的行为。我将之理解为一种精细化的自我锻造:对文体的锻造。而文体永远不会是已实现的、整全的、清晰可见的,它只会是碎片的、未成形的、有待聚合的。」
话语不断地彼此插入、回旋、激荡,叙述与判断层层叠叠,句子始终自我诠释、自我增殖,令黎幺的文体独具一格,他的小说呈现出独特的气质。黎幺层出不穷的比喻予人深刻印象,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他的书写由此实现了德勒兹所揭示的:
「在语言中发明一种崭新的语言,某种意义下的外国语」「揭露文法与句法的崭新威力」「将语言引往其惯常的沟渠之外」。
黎幺的小说让寻常物嬗变,褪下它们陈旧的语言紧身衣,使之获得飞翔的自由。密集而精彩的比喻,常常使评论者失语:除了摘抄引用,别的恐怕都是多余的!
「棍头劈空的劲风如同透明的猛兽……一种战斗本能使他把最平常不过的社会交往都变成了动作电影。」
「星星像眼泪一样落下来……微风令河面泛起波纹:一个细节的复数衍生,如同鳞片。河与鱼之间的包含关系因为这种拟态而加倍成立。水像一条珠链,将河边小饮的梅花鹿穿成一串……蛇像柔软的、贴地飞行的竹笛。」
「像腌生枣一样把一千个弟子浸泡在他的教诲里。」
「孙像是一个噩梦中的变态爱人,挥舞着如阴茎般伸缩的棍棒。」「他的房间很小,他几乎将它穿在身上。」
「我们像从有破洞的袋子里漏出的豆子,滚落一地。」
「此时的他已被驯化,像一批上了英文嚼子的马,匍匐在官方语言的市内环境中。」
「对于床的记忆慢慢地从身体里涌出,包裹着他,先生感觉自己像一条鱼或者一只鸟,在一种四处不着力的舒适感中漂浮。」
这些随处可见且令人可喜可愕的比喻,它们如此丰富,在熟悉和陌生的感觉之间一再转换,紧锣密鼓却不惹人生厌,它们不会使我们罹患词语的「密集恐惧症」,而是刷新了我们对事物的感知,重构了我们关于词与物的想象,让我们与陈词滥调挥手告别。
「……让这颗富含维生素的星球被一种不可阻挡的宿命所震撼。它发现自己正被急剧地削弱,这种强横的、霸道的消逝过程,令它无比感伤,但又觉得无比可笑,就像一道无法随生命一同终结的目光,不得不注视着自身的腐朽。」
你能想象这段绝妙的描写,只是关于一个苹果被放进榨汁机后的命运吗?通过对孩子细致观察与描述,黎幺剥去了盘踞在我们心中的傲慢与偏见:
「其实正好相反,是孩子惯坏了身边的大人。为了被纠正,他们才不断地犯错误,每个孩子都是一部关于错误的百科全书,当然,他同时也是一部关于原谅的百科全书。大人总是正确的,我们通过原谅孩子神话自己,没有任何自信比得上在孩子面前的自信。」
黎幺如才华横溢的诗人般,在任意事物之间灵巧又高速地建立链接。想到这,我们突然明白为何黎幺对法力无边、变幻莫测的孙悟空情有独钟、痴迷不已。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作家将始终渴望在文字中也像孙悟空一样桀骜不驯,但又易如反掌地驾驭万物。于是,黎幺大胆写下这样的句子:
「宇宙的始与终,它的爆发与收缩,只不过是真空二极管的射`精行为,一种点、线、面的维度游戏,实现于一只方块眼球、一个色彩盒子之中。」
另一方面,这些新鲜的比喻,并非无关宏旨,它们不是肤浅的炫技,而是紧密地内嵌在黎幺的文本中,是应书写节奏与意图的内在要求而生。他在刷新事物与词语的过程中,小说也悄然完成,我们的阅读在喜悦与眩晕中结束。
「只有写小说,恐怕才有机会,写我以为自己都不可能会知道的。巫之为巫,也许是在能够动员到那未知无名的世界,将之唤出,赋予形状和名字。」
朱天文的这段话,使我终于理解为何黎幺将《纸上行舟》称为小说。尽管黎幺不认为「写作是一种『出窍』的行为」,但他的小说却时时让我们离开原本固守的位置。
作者:嵇心